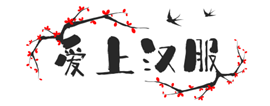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主要是看到前几天在苏州举办的溪山论坛的一张大合影,在心里很有触动。我虽然没有数具体的人数,但是那一眼看过去男同袍和女同袍的人数是基本相当的,欣慰之余就很感慨。想起这些年参加的汉服活动,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是女同袍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的,尤其是有一次外出“踏青”后,我在一位稍迟点加入了活动的男同袍朋友圈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对我的打击不小。他说,“由于我的加入,现场的男女比例立刻从15:1调整为10:1。”当时参与人数共33人。从此以后我也就对海内外举办的各类汉服活动参与人数的男女比例更为留心一些。

一是出于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尊心。
其实汉服活动这几年越来越阴盛阳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汉服的制作变得越来越美观了,因此从梳妆打扮上就能比靠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情怀更容易吸引到人,就更容易有很多爱美的女孩子参与到汉服运动中来。
然而要知道,我们汉服运动发展初期可不是像现在男女比例这么严重失衡的,尤其以08年之前为主的汉网那些老前辈们。再进一步说,如果当时那些拥有强烈汉本位思想的老前辈们男女比例大约就是1:1, 而我们当下的汉服活动男女比例却变成了1:10,就算汉服同袍数量每年都在成千上万的增长,当下的同袍之心,真的与汉网老前辈之心是一脉相承的吗?那么谨慎起见,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统计同袍人数的数据上抹去一个零才更加趋于真实数据?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如果我们现在的汉服运动吸引来的人数绝非偶然的呈现男少女多的趋势,那么一定是我们的宣传和活动在哪里出了问题,甚至有走偏的危险。这些年来,我不断看到很多元老级的同袍心寒宣布退出汉服运动,或者一些同袍还会表示自己“半脱圈”、只做野生同袍(即不参与任何汉服组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同袍,尽管他们对于汉服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却对目前社会上汉服界的种种乱象感到痛心又无能为力,百般失望之下选择退出,他们并不是因为“玩”汉服玩腻了就放手过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太爱汉服运动了才不忍心置身于浮躁、重利、流于形式的乱象之中。他们的做法,我是从感情上非常能够理解的。
太多的时候,社会对于一个男性的期望是成就一番事业,而对女性的要求则是外貌的重要性大大压倒其它方面。回想起我这些年来参加过的汉服运动,姑娘们的妆发都精致复古、形制搭配也十分讲究,一眼望过去真个是乌鬓如云、环佩琮铮,容止国色、恍若神宫仙子,直教人有“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感。这固然是汉服运动的考据复原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同袍当然不希望看到一个影楼装、窗帘布群魔乱舞的活动招摇过市,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上穿的汉服精致程度皆为复原级别,而汉服其它方面的知识水平达不到一个平均线,这岂不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内外失衡吗?既然妹子们对于研究妆造外形方面都能静得下心来潜心钻研、翻阅冷门的古籍,一遍遍上妆卸妆依然兴致浓厚、不厌其烦,却对现代汉服复兴的意义甚至头脑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于“汉服是如何消失的”这段历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么只能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讲女权主义,最不能失掉的一个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等量匹配,仅强调权力不承担义务是不合理的。然而这些年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又因为一些以咪蒙为代表的自媒体营销号善于迎合女利主义心理并进行精准投喂,这些动辄阅读量10w+的爽文给女权主义蒙上了理所当然的污名。其实“女权主义”并不是什么外来的西方才有的运动,也不是什么冲击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洪水猛兽。女权者,女性固有之权力与义务也。女人是人,而人又构成一个民族,那么一个民族里只要包括有女子,一个家庭里包含有母亲、姐妹、女儿,那就可谈女权。再者,像中国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小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繁荣,这个时期民间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开放而进步的权利意识,更出现了很多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思想家。像《金瓶梅》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孟玉楼丧夫后要改嫁,亲戚及乡邻都赞同,说:“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
我们也确实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如果明朝没有灭亡或者明朝之后很快由一个传承华夏文明的汉人政权接替了中国,那么像明末清初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等人也定会不断涌现,那么他们对于中国乃至近现代的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影响就实难估量了。
那么回到现代汉服运动来讲,如果女同袍的关注点永远只在化妆搭配这些事情上打转,关注的眼界永远不会跳出“购入好看的新款汉服—做造型—外拍—秀照片—立刻出掉只穿过一两次的汉服—再去寻找上新的汉服并进行新一轮的秀衣”这样的一个循环,让男人来操心汉服运动的发展方向、形成汉服与其它学科相互交流的各种意见、进行严肃的考据工作、在社会上与成熟的机构寻求合作,不仅辜负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成为汉服同袍本可以发挥出的人生价值,更从绝对人数上带偏了汉服运动的走向,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汉服的复兴之路走得更加曲折,贻害无穷。
二是出于对汉服运动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不忘初心”、发展道路不走偏的思考。
孔明先生在后《出师表》中有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我一直相信《后出师表》是孔明先生亲作而非后人伪作,所谓时危见臣节,此句真国士之言、有大儒风骨。)
“问题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曾经的“汉服”动向不成气候,而在完全没有“易服”之社会需求和政治压力的如今,汉服运动却如火如荼?答案就在互联网。新时期的汉服运动,从一开始就滋生于互联网,借助于互联网、依托于互联网、成长于互联网[8]。”
民国初年小规模复兴汉服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这个锅真的不能扣在“当时没有互联网”头上。周星教授也认为刚刚结束满清统治之后的中国积贫积弱、客观上不具备全国性质的考据和复兴汉服的资源,这一点我比较赞同。但是我认为五四运动为主的社会舆论的走向也挤压了当时汉服复兴的空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引进当时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的概念,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还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力图将儒学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官方意识形态降格回只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门显学。当时虽然也有排满情绪的存在,又因为可以穿西服,并非满、汉装束二选一,又因为汉服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发展中已经融入了太多诸如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精神,那么在当时号召“新文化”的一个社会语境中,复兴汉服的运动倍受冷落、难成气候也就不难理解了。
互联网这些年在中国国内迅速发展、拥有众多网民这是事实,但是互联网的普及与汉服运动的兴起并不存在什么强烈的因果关系。现代汉服运动虽然发生在21世纪,但是其本质与我们汉族人祖祖辈辈都是一脉相承的。互联网不过是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工具,它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价值导向,只要实行剃发易服的满清政权不复存在了,汉族人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自然会想到要复兴汉服。即使没有互联网的出现,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可以传递信息的办法,发传单、办讲座、登报纸、出书……哪怕是口耳相传,效率也许低了一些,但是真正有心复兴汉服的人以非互联网模式传递信息的努力一直都是存在的。
称汉服运动为“亚文化”,其内涵与称汉服运动为“圈子”有着微妙的联系。如果一样事物是你与生俱来的、不可磨灭的属性,比如民族,那就不能叫圈子。一个人生来就是汉族人,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生到了汉族圈子里”这种说法。“圈子”的实质就等同于偏安为亚文化、与社会上可能存在的其它大大小小的亚文化圈子在性质上处于平等并列状态。汉服运动从来也没有满足于只是处在一个“亚文化圈”、跟其它服饰圈互不干涉的状态。复兴汉服的初衷,就是要一个被认可了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地位。
汉服运动是一个民族性运动,如果汉服同袍自己都满足于只是将汉服营造成一个亚文化圈子、圈内人士可以关上门来自娱自乐,那么我们从根本上就没有完成复兴汉服的历史使命,汉服运动实际上沦落成了早已出现的古风大圈子里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庸支脉。更何况,汉族人如果自己都承认自己的文化乃是亚文化,那么什么是“主流文化”呢?我们汉族人又何以有资格称自己传承五千年文明、从未断绝?这样讲来从哲学上都存在矛盾,我们甚至都无法解释自己为何是汉族人。周星教授的文章中认为,“以民族服装而言,所谓的主流意识就是倾向于把唐装、旗袍也视为是中国人的民族服装”, 我觉得这里对于主流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目前中国人除了明确拥有自己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以外,其实主流意识是不具备确切的“民族服装”这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