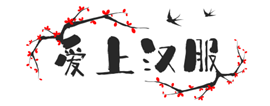清末民初以来中式服装的发展历程
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和变迁。以服装的变革为核心,中国民众的身体形象、自我认同、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均出现了彻底的改观。服装的变迁既是人民日常生活层面不断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及意见人士热衷于争执和倍感焦虑的话题。以服装表达主义者有之,以服装表现身体曲线者有之,反对以制服束缚自由者有之,致力于服装复古者有之,主张全面洋装化者有之,慨叹某些较大尺度裸露的时装有伤风化者有之。但无论多么复杂纷扰,民众的服装生活尤其在生活方式层面却逐渐地形成了既定而又明确的方向,尽管变迁历经曲折,但以下几个方向相互交织而促成的大趋势却日趋显现:一是西装化和类西装款式的普及;二是中式服装的建构实践不断地在摸索中前行;第三,民众服装生活的自由化和时装化;第四,服装的意识形态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辛亥革命前后的“易服”曾经有一个可能的选项便是恢复古代汉人的服装,但其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潮流均使复古诉求不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是“易服”诉求所积累的张力被“剪辫”运动及其成功所释放,剪辫基本上实现了对清朝暴力统治汉人之身体符号的颠覆。其二,当时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易服”就是脱去满清强加的衣冠,至于换上何种服饰,却未必一定要回归古代,换上西装革履,也是“易服”。第三,积贫积弱的新兴国家,缺乏全民换装的经济实力。第四,若要实现全民换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习俗改革运动,其工程之巨大、之艰难,很难一蹴而就。更重要的则是早在清朝崩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西装化的趋势。新生的中华民国实际上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的格局,汉服显然无法在和西服的竞争中取胜。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民众服装生活方式总体上出现短装化走向,长袍马褂就有了两个分化的支流,一是从长袍发展出了中式长衫,二是从马褂演绎出各种中式短装。无论是礼服、还是常服,抑或是劳作时的穿着,民众服饰生活以约定俗成为原则,同时也在不断地实践着改良和革新,其中包括对服饰自由化和时尚化的追求。老百姓日常的服装生活中还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其他形态,只是它们太过民俗而没有被服制改革所关注。
如果把中山装视为近现代中国服饰文化之西式服装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那么,现代旗袍便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范例。和人为建构的中山装主要是以权力动员来推广,以及充满意识形态属性的符号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从城市女性的穿着实践中自发产生,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初步发展为背景,并最终由社会各界女性的穿着实践所完成。虽然它后来也被南京政府纳入国民礼服,但说到底,它是基于自下而上的穿用实践,这一点和中山装自上而下的推广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旗袍虽然和传统旗袍不无关系,但它们基本上乃可视为是不同的两种服装。现代旗袍不仅在款式上有很多改良,更有对女性身体的表现而不是遮蔽。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女装的重大挑战,其中内涵着新时代女性反封建,追求自由、自主、自强以及平等、平权的现代意识。之所以说现代旗袍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成功范例,除了它与上述表现女性身体的西方服装思想密切相关之外,事实上它也汲取了西式服装的剪裁技艺。对于现代旗袍,不宜执著地用族别意识去理解。若一定要涉及族属,它应该是在满汉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以西式女装为参照,汲取了西式女装文化的若干要素,而在近代中国以沿海大城市的消费社会为背景所形成的一款中式女装。
中式服装里的长袍马褂、中山装和现代旗袍,在民国时期于特定的礼仪性场合,多少可以满足人们通过服装来表现文化认同的需求。但它们与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那些生活贫苦的人们现实的衣着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内地乡村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日常穿着,事实上很难为上述中式服装及其变迁过程所涵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地走向了“制服社会”。以军装、军便服和中山装为主要形制的短装上衣和西裤,逐渐扩散到全社会;除了各地乡间以对襟短袄和大裆裤等为主流的“民俗服装”之外,长袍马褂和旗袍几乎不见踪影。虽然也有列宁服、布拉吉等为数有限的外部影响,但总体而言,服装生活形成了款式和色彩均很单调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服装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改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服饰生活,手工缝纫衣物的传统迅速萎缩。以此为基础,人民的服装选择日益多样化和自由化,时装社会里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巨变。首先,是西服卷土重来,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深度进入中国城乡,为各级层所喜爱,实际上它成为时髦、开放和国际化的符号。其次,是服饰成为个人生活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判断,一般不再对其追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类的批评。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服装生活不仅小康化、也走向时装化,中国逐渐进入到“时装社会”。
伴随着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以及服装生活的自由化,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通过服装来表现民族的自信心和尊严感的社会文化动态。例如,中式服装除了长袍马褂和男子长衫之外的明显回潮,现代旗袍逐渐重回时装市场和各种礼仪场景;肚兜、马甲、围裙、瓜皮帽、以及各种中式短装(袄、褂),包括各地多种多样的“民俗服装”均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以此为资源和土壤,在进入21世纪的时装社会,依然出现了对中式服装予以再建构的尝试,这便是“新唐装”。从一个世纪以来中式服装的发展轨迹看,新唐装是21世纪初又一次重要的建构实践。由于中山装的突然淡出,男性服装的中国属性表象出现了真空,因此,虽然新唐装的设计兼顾女性,为女性中式服装在旗袍之外又增添一款新选项,但它对男性中式服装填补空白的意义更大,是继80年前现代旗袍实现中式服装的西式化改良之后,又一次比较成功的中式服装西式化的改良实践。新唐装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中国人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渴望,也反映了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心。此种社会心理的巨变,正是它得以大流行的根本原因。新唐装的确具备了和现代旗袍相并列的资质,很快就拥有了颇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海内外的高度认知。
“汉服”重现:大规模的草根文化实践
显然,汉服运动实际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面向国内多民族格局下汉民族服装的缺失;二是面向国际社会场景下中国自我形象的焦虑。对于前者,寻求汉服的“姆庇之家”不应被视为狭隘的民族意识。至于现代化、全球化、西化带来的文化认同焦虑,反映在“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之类的表述中。显然,这是对过度西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之倾向的一种文化反拨。
汉服被认为表现了汉民族的性格,诸如柔静飘逸、娴雅超脱、泰然自若,或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等,同袍们用来描述汉服的词汇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主义理解,这和对华夏汉族的本质主义界说互为一体。特别是在华夷对举或中西并置的场景下,汉服的标签、符号意义就会更加凸显。
笔者曾指出,汉服言说和汉服运动的理论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同袍们在户外服装活动中以各种策略、举措和方式所进行的变通及建构主义实践。本质主义的汉服陈述或言说表象,容易形成某种排他性,容易使汉服运动走向和周围服装生活之现实的对峙;建构主义的穿着实践则促成汉服的多样性,在使汉服运动内部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难以形成共识。虽然有人执著于纯粹性的想像,但现实中却不得已或有意识地采取了建构以及容许建构的行为。
汉服在各地社团的户外实践中出现了“祭服化”的倾向。无论是特意设定的祭祀历史上的汉族名人或英雄的活动,还是在开笔礼、成人礼、婚礼等人生仪式过程中的祭祀环节,抑或是在清明、端午、七夕、冬至等许多传统年节时举行的汉服活动中的祭祀段落等,反复、频繁举行的祭仪为汉服提供了出场的必要性,也为所谓“汉礼”提供了复兴的路径和形式。这些仪式,往往被说成是对古代礼仪的“复原”,但它们也属于当代的创意和建构。祭祀活动可为汉服出场凭添某些庄严感和神圣性,也能为很多同袍提供其日常生活里久违的意义。但祭服在活动现场,无论色彩、风格和款式形制却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难以统一。
十多年来,汉服运动已发展成为一个较大规模的草根文化运动,与此同时,它的内涵也日趋复杂。汉服理论家中既有执著于古代形制的考据派,也有致力于扩大汉服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的现实派,亦即主张将汉服改良之后穿用于当代。汉服运动所设定的目标是将其依托古代服饰文化资源而试图建构的汉服,作为汉族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而予以确立和普及。它对唐装、旗袍的排斥是要促成一种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亦即确定反对的目标而强化自身的认同,问题是其认同的实际状况却较为混乱,究竟是汉民族的认同,还是中国人的认同,抑或只是作为亚文化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