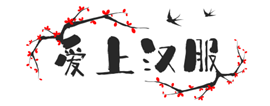余闻:“衣冠原为御寒蔽体之用,苟以为妥,旦且穿之。”余以为此言越时装之潮流,溯衣饰之本源,谏今世之糜风,循质朴之哲信,颇有其理也。
然余复纵观历史,横览世界之时,却觉衣冠之兴替,实非一人一时之事也。一袭衣冠,小可现个人之品貌;大可知黎庶之民情;远可明历史之演化;近可察时势之潮流;分可追宗族之变迁;合可阅文化之交融;别四季以晓天时;适温湿而通地利;数丰俭而识廪仓;度风尚而鉴哲理;古之涉政而立法制;今之育教而竖礼仪;添锦绣而结审美,创新材而适科技……实难一言以蔽之。

且我华夏,盖五千年悠久历史,广九百万域海疆山,度十六朝更替演变,举五十六兄弟共戴,远有文明古国之荣辉,近有豚尾猢服之屈辱,现更有国内权利者,草宣传而误我民识,而外邦异谋者,假伪服而辱我国体。故华夏衣冠之策,更非扼要之句可尽述。
华夏衣冠,以传统汉服为中砥。汉服,上溯炎黄,下禀宋明,一脉传承,丰富多彩而演化有序,正可鉴华夏之风尚。中华,文明古国也。而衣冠之文明多有史证者,盖重衣冠乃上古之风也。自上古文明伊始,华夏衣冠便与其礼法制度息息相关。古有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可见”同衣裳”乃古以为”本俗安万民”之法也(见《周礼·地官·大司徒》)。而<左传·昭公九年》有:“服以旌礼。”之句;《管子·君臣下》有:“旌之以衣服”之说。旧注为:“所以顺礼也”。此正是服饰“礼节”之内容要质。而我国可考之衣冠史证,列于经史子集者,更不计其数。

但余亦知,上古之礼,与今有别,皆因生产之发展,社会之演变,阶级之不存,而衣冠已可使人各求所需,各依所好,实乃民之幸甚也。而余所引上述之说为证者,决非欲复阶级之礼而逆今日之势,只欲明言,我国衣冠之事,自古已有史可查,有证可考,有法可依,有礼可循,上至君主,下至庶民,不论贤愚贵贱,莫不问衣冠之道,而余谓其乃文明之脉,盖不虚言也。
且文明之说,法度之外,衣冠所在,更有民情存焉。
诗经·国风·邶风有<绿衣>之句: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再有<诗经·颂·闵予小子之什>之<丝衣>,<诗经·国风·郑风>之<缁衣>之句,更有包胥泣秦庭而哀公做<无衣>,屈子歌”奇服”而日后投汨罗。由此可见,衣冠之敬,先秦已自有之。而后世之人,于汉服之情浓更盛。余所见历代诗词,仅题中便现”衣”字者,约一百三十首;而如孟郊之”游子吟”者,虽无”衣”字为其题,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之句早已深入人心。更有今人咏衣冠之器重而舒个人家国之情感者,不可胜数也。余每诵其辞,而仰古人之心并思今人之志,更深信衣冠之敬重,可见人心国志也。

汉室衣冠以宽袍大袖为主,较之诸夷宽松舒适,大摆拂风,有天然妙合,晃若仙成之感,国内历代画师皆以汉服为神仙装束,虽满清不易;而西方诸神圣母之服饰亦有此风尚。这不仅因为中原文明较之诸夷先进,而人民生活优逸所致,更乃华夏民族自古崇尚自然,故“天人合一”之哲思亦现于服饰之间,而”仙风道形”之理想更呈于画卷之上。盖汉服之哲,合乎华夏之道,故民美之,而世袭之。 衣冠之变革,可鉴历史之兴替。黄帝制衣裳而万民免存亡之难[3];周公明制式而成后世之常礼;管仲服右衽而孔子贤;晋襄战崤山而缞绖墨;武灵适胡服而赵地强;先唐禁衣羽而生态定……历朝历代,凡制有所变,则衣制亦有所改。但明代之前,华夏衣冠制式未尝变质。元蒙袭旧衣而别汉种,一统不过百载(1279-1367)。满清易汉服而溶华夏,历三百年不废。辛亥革命后,竟仍有张氏留豚尾而复帝制,不顾大势,逆天道,忤民愿,甘效鞑虏,更有类张勋留尾者不只一人,断尾之时竟也有哭天抢地之汉人。

独不思扬州十日,八十万汉血成河;嘉定三屠,千万家积骨如山;留发不留头,清初壮士之节义人皆慨叹;束豚尾跪外虏,明末汉奸之奴颜劣耻人所共愤。盖衣冠之不辨,故种族之不知分,则历史之不考,而家仇国耻尽忘矣。余并不否认清民甘心受辱于满清三百年更有他由,然当稳奴隶之人,不思复国兴族,不辨衣冠之由是为其重中之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