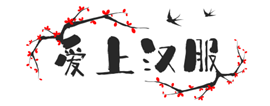一件深衣,一份信仰,一个人。
多年以后,我想我会记得这天,一场盛大的祭礼,一次对儒家文化的呼唤,一群崇尚传统的中国人。
只是,我依然坚持的相信,这是一个人的祭礼——白衣胜雪、不染纤尘。
——摘自方哲萱《一个人的祭礼》
一、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方哲萱25岁。
她说的这一天,是2004年11月12日,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日。
那一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但年轻的方哲萱心里却有些沉重。面对这场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盛大活动,她是有些疑虑的。
虽然“杨柳青”、“妈祖节”以及“祭孔大典”的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方哲萱却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在那一刻,她愈发觉得自己即将的行动,意义非凡。
于是,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用自己一番白衣如雪的祭拜,在满场的顶戴花翎中,只身上演了一场关于汉服复兴的举目壮举。

这场单刀赴会式的祭拜,在当时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但她遗世独立的单薄姿态,以及后来的那篇《一个人的祭礼》,却迅速在网络传播。
2012年9月,在越来越大的“汉服祭孔”呼声下,举办方终于将表演服装改为汉服。
汉服运动,由此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并且迅速收获了一批拥趸。
二、
不过,方哲萱的“只身汉服祭孔”只是汉服运动推进的一个高潮而已,这场活动的肇始,还可以往上追溯。
2003年11月22日,中原大地的郑州街头,阳光正好,秋色宜人。
此时,走在路上的电力工人王乐天的心里是平静的。
虽然他的穿着看起来有些怪异,似乎与周围的车水马龙有些突兀感,但是他很坦然。
就这样,面对路人的议论、孩童的不解,他完成了现代“着汉服上街”示众的一个崭新旅程。
这一天,距离上次汉服以平常装束走在街头,已经三百多年。

应该感谢那位叫张从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是他把王乐天的事迹投诸了报端,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虽然王乐天当时是坦然的,但在报道中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在人群之中,人们把他误解为日本人,而他身上的那件汉服,则被很多人当做“和服”看待。
“在街上,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事后,34岁的王乐天如是说。
这一行,坚定了他推广汉服文化的决心。
这篇报道,把“汉服运动”第一次推上台面,并迅速传播扩大,成为社会公众事件。
2003年,是普遍认为的“汉服运动元年”,自此,越来越多的汉服爱好者走上了街头巷尾。

三、
早期汉服运动的孤独感如果继续往上追溯的话,关于汉服运动的影子还有很多。
比如网友自制汉服,比如网友着汉服束发弹琴——不过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
即便是到了王乐天,到了方哲萱他们这里,虽然汉服运动已经走入了大众的眼帘,但作为身体力行者,他们还是一个略显单薄的孤独群体。
我一直觉得,一件事物有孤独感并非什么坏事。孤独往往会使事物变得纯粹,而纯粹,会使他们变得更深刻。作为草根,王乐天和方哲萱的力量是微薄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思虑的深刻。
而一旦大众抱着“保护”或者“热爱”的善意涌入,试图去拯救或者击碎这种孤独感,这样的深刻往往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我毫不怀疑民众情感的真挚,但对它所带来的影响,我保留意见。
美学家蒋勋先生在说:
“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不能特立独行,那么,艺术和美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我觉得汉服运动也是如此。自王乐天肇始后,十多年的风雨漫滤和大众趋附中,它在众人之间的孤独感已经不再,而它的纯粹感,也已消弭。
击碎孤独感无可厚非,但倘若其背后的纯粹和深刻也随之被击碎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

现代汉服运动的功利化与表演欲十多年过去,“汉服复兴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上演,而各种论调,也是众说纷纭。
一般来说,我们把汉服运动兴起的根本因素都是归结于中华国力的再次强盛。这是对传统文化急切的呼唤,是民族自豪感的回归,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彰显。
自明末清初的“剃发易服,不从者斩”之后,传统的汉服日渐消弭。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小范围的波澜起伏,如袁世凯汉家衣冠祭天,章太炎先生着绣“汉”交领衣,张大千先生宽袍欧洲游等等。但这些都是个体在时代中的高蹈独舞,终究未能使“汉服复兴”锋芒毕露。
所以,真正让汉服运动勃起,乃至让传统文化回归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恢弘所致。
但我们如今的时代又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所以,汉服运动的推进,因为其民间性和实验性的性质,或多或少地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悖初衷的行为出现。
白建军先生在《从胡服骑射到汉服运动——试论服饰改革的原动力》中谈到:
“由汉文化爱好者自发倡导组织的汉服运动,虽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复兴传统文化的服饰诉求,但由于巨大的时代落差,注定了它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命运。”
这话一语成谶。纵观当今之“汉服热”,大众的热捧和附和背后,沾染了太多的功利性和表演欲。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有需求必然就会有逐利者的涌入,汉服热也不例外。
市场经济下,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抵制。
但是,商家的炒作过多地关注于服饰的本身,而对于汉服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却关注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感到沮丧的现象。
有次在夫子庙景区,看到几位身着汉服过市的姑娘。我问她们穿汉服的初衷和感触,一个说衣服好看,穿在身上回头率高;一个说商家宣传,古装价格实惠,穿着也个性。
那一刻我觉得是悲哀的。我们可能只是捡起了一件“汉家衣裳”,却没能重拾起它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这是商业功利化的必然,也是文化疏离感的悲哀。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日之“汉服热”,终究未能让众多民众从根本上了解我们姓甚名谁,我们来自何处,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流于了表面。

这样的悲哀还体现在一些没有节操和底线的无知行为上。
2004年10月6日,河南丁晓棠(网名“寒门仕族”)、深圳的王琢及其妻子郭丽红(网名“晨澍”),身着汉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物。
次日,《京华时报》以《汉服集会》为题材发摄影报道称“昨晚,8名儒生打扮的青年……身穿‘汉服’走向王府井,他们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对汉民族特色服装‘汉服’的记忆。”
然而,当日晚,一些国内网站的论坛上却显示另一条被伪造的虚假报道,标题为“《寿衣上街?改革开放多年,封建迷信上街》”,上写:“昨晚,8名寿衣打扮的青年……身穿寿衣走上王府井,他们希望能够为恢复传统的殡葬业做出贡献。”——摘自《汉服复兴大事记》
这无疑是一场博眼球没底线的操作,背后是关于流量和商业利益的博弈。
虽然最后对簿公堂,汉服青年以胜诉告终,但对于“汉服热”来说,无疑不是一次荆棘刺脚的疼痛。
“汉服热”背后的功利性,是汉服运动突进过程中的一大败笔。

这是一个戏精丛生的时代。
戏精们似乎对那些流行的、能够快速吸引众人耳目的热点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嗅觉。
当汉服运动由一场孤独的心灵回归,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民狂欢的热点之后,戏精们也开始按捺不住,纷纷披挂上马,逐鹿江湖。
于是,地铁上、机场内、商业区……但凡能够吸引巨大流量的场所,都成为戏精们发泄旺盛表演欲的所在。
当然,表演只是手段,背后的流量收益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至于汉服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他们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不明所以的。
于他们来说,所谓的汉服运动,只是一场古装的cosplay。
他们与当年的王乐天和方哲萱们不同,他们缺少前辈们的孤独感和责任感,他们更需要的是众人眼光聚集,那些背后的东西,他们未曾关心。
我只能说,这是一场“知其然”的狂欢,却也是一场“不知其所以然”的悲凉。

四、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服”到底是什么,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吧。
汉服的含义其实“汉服”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
在蒋玉秋等编者所著的《汉服》一书中认为:狭义的汉服是特指汉王朝这一时代的代表性服饰,它的内涵比较单一,强调的是大一统时代民族服饰的共融;而广义的含义是指上下五千年中整个汉民族的服饰,它是具有连续性的一个发展过程。
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现在的汉服运动中所指的汉服,应该是广义的汉服。
汉服的发展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华夏衣裳由黄帝所制”,黄帝垂衣而天下治,汉服自此初备形制,并绵延千年。
“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司马迁《史记》
到了商周之际,服饰开始与礼制挂钩,形成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自此,服饰不再是单纯的遮身蔽体的功用,服装的文化意义也开始日趋完善。“乘殷之车,服周之冕”成为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