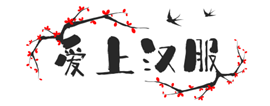文明如何开始?
历史在幽暗中被逐渐照亮。盘古开天辟地是其中第一次。现在我们要说的,便是盘古之后不知多少世代的事了。天地虽已开辟,人却仍不免混于兽迹之中。“羽皮 革木以御寒暑”,如此而已。世上分居各地的人类,还没有显着的族群差异。我们将发现,人们首先想到用以区分族属也区分文明与蒙昧的,是服装。
1.垂衣裳而天下治
照亮历史的火炬点燃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语出《易·系辞》。作为“天下治”的前提,“垂衣裳”这个意象显出强烈的象征性。
“垂衣裳”之后两千年,又有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也因此成为汉服的起点。
“盖取诸乾坤”一语表明,华夏服饰超出了仅仅遮羞御寒的实用性,还体现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乾上,坤下,如同上衣下裳。由乾 坤,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阴阳、天地、男女、父子、君臣等概念。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先民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 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才是《易》的本 意。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垂下双手,无所事事的解释。意思是,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此衣得名来自掩蔽人体严实之故。《五经正义》说“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 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如在制作中,先分裁上衣下裳,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深衣 的下裳以十二幅度裁片缝合,以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垂直的背线以示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公平。
出于这些对天人秩序的表达,也出于“完且弗费”的现实考虑,深衣得以“先王贵之”,并发展为超越阶层、职业、性别的大众常服,影响深远,成为历代汉服中最持久的线索。
2. 如果没有管仲
夏商时期,农耕上升为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到周代,华夏族与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有了明显的不同。服装因其直观性,成为古代华夏族借以区分 族属特征的主要标准。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农牧冲突,用一句话概括——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的。这种现实刺激了华夏的民族情绪之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春秋五霸出现了。他 们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攘夷”的内容。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 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
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管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周王的权威不断低落,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整个华夏族。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的评价是文化意义上的。管仲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就主要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夷狄服装左衽,与华夏汉服的右衽相反;夷狄批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所以两者的形象很不相同。
有了管仲,汉服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
3.胡服骑射之辩
进入战国以后,诸夏自身纷纷进行了大改革。历数重要的变法,从魏国李悝开始,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这些变法都要求取消封建制,实现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官僚制取代世卿制,同时不同程度地执行耕战激励,使国家机器尽可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所以称为战国。
列国变法中,尤以赵国胡服骑射最有个性。应当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并不是要将赵变成一个胡人国家,并不是华夏族向胡人的归化。实际情况正相反。
赵武灵王继位以后,赵基本不再参与中土战国争霸,其战略重点转向北方,经略诸胡部落。赵在北方的威胁并不在于胡(匈奴),而在于中山。就血统而论,这虽 是一个白狄人的国家,到战国之世,却已被视为中土战国之一,可知其华夏化的程度。同春秋时的中土夷狄一样,中山并不以骑射见长。骑射术实际上来自于胡。
问题是,诸胡部落对赵国边地的攻击没有达到需大规模出兵的程度,充其量袭扰而已。所以胡服骑射并不出于对胡的惧怕,而是主动借助胡人军事技术的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
胡服骑射另一个目的,在于招徕胡人。赵武灵王曾以舜和禹的事迹自喻。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国而裸国化,武灵王以此类比,表明自己利用胡服教化胡人, 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的心迹。事实证明这个预定目的达成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缩小,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 烦王致其兵,两族归顺,为赵国提供了疆土和大量娴熟的骑射士,奠定了赵的强国基础。
胡服骑射的范围如何?《战国策》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似乎百姓也在变法要求内。但是我们找到了比这更早的史料《竹书纪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谪子、戍吏皆貊服。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受命胡服的范围,只限于将军、大夫、谪子、戍吏这四种人,不包括赵的百姓。而这四种人,都是国家从上而下的各级军事头领。同时,作为胡服骑射据点的“骑邑”,只设在北方边境,内地并无设置“骑邑”的记载。
这说明胡服骑射的重点只在骑射,在伏胡,在军事上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应用。所以百姓不必胡服,内地不必胡服。胡服并没有大行其道,赵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赵人依然是华夏族的一支。
实际上,骑士所穿窄袖短衣,是夏商以来华夏族的固有样式,不见得来自胡人。“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解释说,“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他进一步认为,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 士的一般衣着,只是加入了一些胡服的元素。
战国时期的各国战士,就是穿着这样华夏固有的窄袖短衣走上战场。面对奖励耕战、君主集权、骑射作战的新华夏,四夷不堪一击:
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4.孝文帝的理想
汉服的第二次危机,来自于五胡乱华。
自战国驱逐夷狄、尤其汉朝压倒匈奴之后几百年间,汉人一直对四夷保持巨大的威慑,直到西晋瓦解。人数众多的游牧民进入中土内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 绝若线”的局面重现,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连同汉人的生活方式、汉人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受到大破坏。胡汉相攻,中土之地称为“陆沉”。
除南朝外,汉人社会向两种地方收缩。其一,世家豪族所建立的坞壁;其二,流民聚集的河西。经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汉服椎髻赖以保存。这时胡汉二元对峙局面遍 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这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鲜卑君王——他有一位汉族母后冯氏,她重用汉人、崇尚经学,更重要的是给了小国君以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使他虽为胡人却有了汉 心。这就是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长背景。冯氏执政期间曾设立皇宗学,使皇族子弟入学,孝文帝在这里培养为一个以经为准则的君主,一批鲜卑贵族子弟,尤其孝文 帝的兄弟们也成为日后汉化改制的得力助手。
孝文改制的目的,即在于选择用夏变夷之路,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更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汉化令开始颁行——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类似商鞅徙木立信,要借以宣誓决心和威望,也有试水的意图。这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 “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